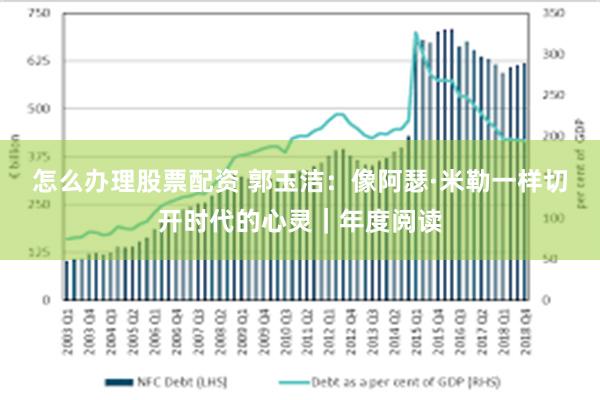
1怎么办理股票配资
回看2024年的阅读,有点意外,最令我受益的竟是剧作家阿瑟·米勒的自传《文学的一生》。

说意外,是因为提及阿瑟·米勒,人们先想到的大多是他和玛丽莲·梦露的婚姻八卦,因此很难去认真对待他的文学成就。另一个原因则是由于剧作家的独特性,他们的作品不止于案头,而要经过舞台实践和多工种配合,才能最终实现,很多时候,剧本都会沦为次要因素,而那些文本性太强的作者,又常常很枯燥。这次阅读阿瑟·米勒的自传,以及重读他的剧作集,我才发现他的作品是如此动人,它们兼具了舞台想象力与文学性,而阿瑟·米勒本人,则是一个极富艺术个性、又有深沉社会思考的时代巨匠,在他身上体现出了文学艺术真正的可能性。
阿瑟·米勒出生于1915年的纽约,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祖父和外祖父都从事服装生意,他回忆道,小时候住在哈莱姆区的公寓六楼,窗外就是美丽的中央公园。但是,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改变了一切。外祖父破产后,失去了住房。米勒家也每况愈下。他们辞退司机,卖掉豪车,房子变小了,度假的平房也用不着了。哥哥从纽约大学退学,去父亲的成衣厂帮忙,父亲越来越沉默,午睡时间越来越长,而母亲靠变卖珠宝,维系着家里的生活。
这场悲剧不只属于他们一家,米勒说,走在大街上,到处都能看到空空的店铺,窗上贴着“出租”,还没关门的商店也没有顾客,几乎每栋公寓都永远贴着“有空房”。
经济危机带来了普遍的心理危机,他写道,根据报道,大萧条期间仅纽约就有将近十万人精神崩溃。他们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希望,失去再次相信的能力。
大萧条,那种上升的年代突然下坠——也就是“美国梦”破灭的感觉,成了阿瑟·米勒成长中的底色。他陆续听到身边有人自杀的消息,都是一些乐观自信、一切向好的年轻人,死亡似乎还遥不可及,就突然到来了。而在他听说的三起自杀中,两个就是推销员。推销员,这是一个很具美国特色、也非常男性的职业,他们开车四处旅行,见多识广,对于童年的阿瑟·米勒来说,这些男性长辈充满了传奇色彩,也是因此,他们的死亡和失落在他心里留下了长久的疑问。

1948年,阿瑟·米勒在康迪涅克的小屋写出了《推销员之死》。次年,这部剧由伊利亚·卡赞执导,在费城首演。米勒常常讲到首演后的场景:帷幕落下时,没有掌声响起,奇怪的情绪开始在观众中弥漫开来,有些人站起来穿上衣服,又坐下,有些人——尤其是男人侧身捂脸,其他人则毫不掩饰地哭泣,然后,他们想起来要鼓掌,掌声经久不息。在后台,米勒看到一个老年男子,那是一家连锁百货商场的总裁伯纳德·金贝尔,有人告诉他,那晚金贝尔回去之后下令说,百货商店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因为超龄而被解雇。
毫无疑问,虽然大萧条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战后的美国经济即将腾飞,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但是曾经的下坠给几代人都留下了深刻的伤痕。不仅如此,这一内在于资本主义自身的危机会不断重来,在新的一代人身上留下伤痕。《推销员之死》并没有过时。
2
大萧条使原本不关心政治的人们开始思考,世界怎么了?我们应该怎么办?那时,16岁的阿瑟·米勒在看球赛的时候第一次听到了马克思主义,一个大学男生告诉他,尽管肉眼看不太清,但是社会上的确存在两个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现在全世界正在兴起一场革命,势如破竹,到时物质将会进行平均分配。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阿瑟·米勒实在难以接受,这些话和他从前听到的都不一样,可是,他的灵魂又被深深地震撼了。1930年代,社会主义浪潮在全世界涌动,阿瑟·米勒成长其间,此后终其一生,他都被视为一名左翼作家。
可是“冷战”开始后,阿瑟·米勒的左翼身份遭到了双重危机,一方面是在美国国内反共运动(即麦卡锡主义)的攻击,另一方面,苏联阵营传来的消息也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在自传中,阿瑟·米勒花了许多篇幅来自我对话,从这些对话中可以看出,米勒更认同的是一种朴素的信念,那就是来自1930年代的经验:那时原本不关心政治的人们逐渐认识到,为了度过贫穷和动荡,他们必须团结起来,互相帮助,由此应运而生了工团主义、联邦政府的系统救济、农场合作运动,等等。也是因此,他对六十年代崇尚个人自由的学生运动很不以为然。
左翼在阿瑟·米勒身上的另一个表现则是,他坚持艺术与社会的密切关系。他说,一个剧本,应该让普通人也觉得有意义,“唯一值得为之付出努力的挑战,是最广泛的和最崇高的,即民众本身”。

在阅读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阿瑟·米勒戏剧经典》时,我为每一部剧作所触及的问题之巨大、之深重而震撼,大萧条、战争、移民、猎巫……每一个都是社会性的重大危机,却又如此切实可感,毫不教条,通常故事就发生在一个或几个普通的家庭,通常就集中在父子之间。社会危机从外入内,侵蚀着人的心灵,阿瑟·米勒活生生地把这一切切开了。
这样的艺术信念,是阿瑟·米勒的创作如此成功的内在原因之一,却也为他招来了麻烦。1950年代初,参议员麦卡锡发起了清查共产党的运动,他自称手握黑名单,要人们互相揭发。一时间人人自危,到处流传着背叛和告密的故事,人与人之间相互怀疑、警惕,很难再互相信任。阿瑟·米勒拒绝出卖别人(因此还曾被判“藐视国会罪”),却也为那样的社会氛围而痛苦不解,他想到了17世纪曾在萨勒姆发生的猎巫事件,也许可以写一部这样的作品,用过去来讲述现在。
在筹备新剧本的过程中,1952年4月一个下雨的早上,米勒开车去了伊利亚·卡赞家,在那里,他得知卡赞为了保全自己的职业生涯,向非美委员会提供了几十个人的名字。卡赞是米勒的老搭档,他曾在1930年代加入共产党,作为一名左翼导演,他曾在“团体剧场”中引入斯坦尼斯拉夫体系,并倡导在戏剧中表现社会议题,后来,卡赞成了好莱坞的著名导演,但是麦卡锡运动中的告密行为,为他留下了毕生的污点。
离开卡赞家时,卡赞的妻子莫莉问米勒接下来要去哪里。米勒说,他要去萨勒姆。他回忆道,莫莉立刻明白了这个含义,她睁大了双眼说:“你不要把这个同女巫相提并论!”
米勒完成了剧本《萨勒姆女巫》。可以想象,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中,舆论反应非常冷淡。但是随着时间过去,在所有阿瑟·米勒的作品中,《萨勒姆女巫》最广泛地被搬上世界的舞台。所有压制异己、充斥背叛和恐惧的地方,都能在这部剧里看到自己熟悉的生活。
3
2005年2月10日,阿瑟·米勒去世,终年90岁。法国人弗里德里克·马特尔在《戏剧在美国的衰落》一书的开头写道,阿瑟·米勒去世的那个夜晚,百老汇所有剧院都拉起幕布,向这位剧作家致以一分钟的默哀,同时,时代广场所有舞台的灯光都调暗了。纽约的寒风中,这一举动令人们激动不已,它让所有剧院成为一个团结的集体。
但是,讽刺的是,作者写道,这些剧院早已不再排演阿瑟·米勒的作品,甚至几乎完全终止了剧本戏剧的演出,“阿瑟·米勒死了,更加令人伤感的是,那似乎也是戏剧的死亡”。
在这本书里,作者勾勒了美国戏剧的历史。在1940~1950年代,阿瑟·米勒和田纳西·威廉斯这两个大剧作家的出现,象征着百老汇——也就是当时的美国戏剧在创作上最辉煌的时代。接下来,随着各类基金、企业的支持,全美很多城市、大学都建造了剧院,戏剧成为城市和社群的一部分,很多剧作家投身期间,关注当代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创作新的故事,一直到1980年代,美国戏剧文化发展都十分蓬勃,观众数量增长极为迅速。
和很多艺术门类一样,从一开始,戏剧就兼具了商业和文化两个属性,如阿瑟·米勒所说:“戏剧一直是一桩生意,但它曾经是一门艺术。”很快,商业属性就压过了文化属性。戏剧的成本不断上涨,包括剧院租金、营销费用,为了盈利,首先压缩的是制作成本,原创和实验越来越不可能,也不会花很多时间来打磨作品,热爱戏剧的独立制作人难以为继,戏剧从业者纷纷改行,加入资本雄厚的影视业,戏剧业渐渐被抽空了。
1990年代,迪斯尼进军百老汇,开发出大制作音乐剧、电影IP、巡演的模式,百老汇正式变成跨国公司和房地产商的天下、影视业的附庸,舞台上演出通俗易懂、保守的故事,票价上涨,观众只剩下看得起戏的中上阶层,和到此一游的游客。
在这种时代变迁之中,书中说,1970年代,阿瑟·米勒的戏还如日中天,1980~1994年,百老汇一部米勒的戏都没有上演。
作者问道:“如果一种文化没有能力进行创造,只能进行再创造,没有能力发明,只会重复,没有能力制作,只会复制,这叫什么文化呢?如果我们还没有去看演出,就提前知道这个演出讲的是什么,这叫什么演出呢?”
为了抵抗百老汇的过度商业化倾向,美国戏剧人发展出了外百老汇(Off-Broadway),他们选择在较为边缘、房租便宜的格林尼治村、soho和东村,演出非营利性的小剧场戏剧。后来,又出现了更激进、更叛逆的外外百老汇(Off-Off-Broadway)。
在这样的戏剧场所,通常上演的是先锋戏剧,创作者、各类异见群体大胆创新,他们在街头、在咖啡馆演出,尽情颠覆主流戏剧和主流美学。可是,作者说,先锋派变得越来越激进,他们主动地将自己和大众隔离开来,这种自卫式的创作方式,使得观众越来越少,在很多演出中,创作者甚至比观众还多。
在这样的戏剧潮流中,晚年的阿瑟·米勒同时面临两个层面的困境,一是来自百老汇的商业戏剧对他的漠视,另一重则是后来的先锋戏剧对他的解构和嘲弄。
阿瑟·米勒已逝,这些已不是他的问题(事实上,阿瑟·米勒直到晚年仍在坚持创作,保持着很高的水准,并在欧洲受到广泛欢迎),而是今天我们共同的创作困境。
4
阿瑟·米勒去世时,我正在一家杂志负责“讣闻”栏目。1500字的篇幅,只能重点介绍一部作品,于是在他众多的剧作中,我选择了《推销员之死》。杂志问世后,我收到一位前辈的批评,她认为,重点应该放在《萨勒姆女巫》。我明白了,经历过那十年的她,更熟悉猎巫运动的伤害,而在日益商业化的社会氛围中成长的我(和其他年轻同事),更能体会《推销员之死》带来的不安。阅读中想起这一往事,让我再次感叹,是多么厉害的作家,竟然书写了20世纪的两大主题,并且都写得如此出色。
自传中,阿瑟·米勒也回忆了1980年代中国上演《推销员之死》的故事。那时著名演员英若诚出演了主人公威利。米勒没有想到,威利自欺欺人的辩白,“我不是大路货,我是威利·洛曼,你是比夫·洛曼!”在当时的中国几乎像是革命宣言,一名年轻的中国学生在剧院大堂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说:“我们被打动了,因为我们也想当第一,想变得富有和成功。”那时的中国刚刚走出长期的匮乏,人们渴望成功、渴望富有,渴望物质繁荣。米勒说,没想到,他在1948年的康涅狄克给1983年的中国发出了个人主义复苏的信号。
但是终有一天,我们会理解《推销员之死》,就像理解《萨勒姆女巫》,以及理解阿瑟·米勒的其他作品。
阅读阿瑟·米勒的自传和剧作集,让我对他肃然起敬。很久没有看过如此严肃、充满道德责任、却又动人的作家了。比起阿瑟·米勒晚年,短视频时代的文化更为碎片化,也更为娱乐化。人们随时都在享乐,却又感到深深的抑郁和无力。创作者要么迎合这一趋势,去制造碎片,拼贴碎片,要么堆叠技巧,自娱自乐,即使那些有时代关怀的创作,也丧失了历史的纵深感,变成另一种正确、光滑的碎片,无法呈现出深重的危机和复杂的心灵,也就失去了面对真实问题的能力。
在满地稍纵即逝的碎片中,我深深地感觉到阿瑟·米勒的珍贵。今天我们需要的这样的整体感,需要在历史中承担起个人的责任,将过去作为理解未来的方式,不停歇地去感受、思考,直到寻找到对的方法,像一刀切开夹心蛋糕,或者像一条小路切穿大山地层一样,像阿瑟·米勒一样切开时间,切开时代的心灵。
举报 文章作者
郭玉洁
经济人的人文素养阅读 相关阅读 云也退:阴谋论为何永远有市场丨年度阅读
云也退:阴谋论为何永远有市场丨年度阅读媒介技术和工具不只是把人的注意力开发为商品,它们还发掘出人在懒惰这方面的潜质。人如果能够放弃表达,如果工具能笑得比你更彻底,更撕心裂肺,人就会放弃笑。
30 01-27 12:34 《不眠之夜》上海版八周年:接待62万人,总收入5.5亿
《不眠之夜》上海版八周年:接待62万人,总收入5.5亿据统计,《不眠之夜》上海版项目总收入超5.5亿元,接待来自全球各地观众超62万人,其中跨省市及境外游客占比60.5%。
245 2024-12-18 13:44 71岁法国影后于佩尔,在北京上演《玻璃动物园》的故事
71岁法国影后于佩尔,在北京上演《玻璃动物园》的故事她多次来到中国,也喜欢看中国电影,随口就说出毕赣、刁亦男、娄烨和贾樟柯等文艺导演的名字。她设想自己能参演某部中国电影,那会是她漫长艺术生涯中一个有意义的尝试。
90 2024-12-06 12:32 历史上,美国为什么会放弃“贸易保护主义”的长期国策?
历史上,美国为什么会放弃“贸易保护主义”的长期国策?美国历史上长期实行高关税保护主义,二战后转向自由贸易是为了拉拢盟友和扶持战败国,冷战是推动全球贸易的重要原因之一。
60 2024-11-29 17:43 一人饰演15个角色,木偶剧也能传递深刻的人类情感
一人饰演15个角色,木偶剧也能传递深刻的人类情感来自柏林德意志剧团的偶剧《卡尔·博姆》怎么办理股票配资,是乌镇戏剧节“特邀剧目”中最特别也最触动人心的剧目。
23 2024-10-30 17:31 一财最热 点击关闭